预算法修订再度搁浅
财新记者从全国人大相关部门获悉,将于12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,议程中不会安排审议《预算法修正案(草案)》。修法小组政府部门成员中一位官员告诉财新记者,二审后没有见到有新的修订草案成型,预算法修订将转交下届人大完成,本次修订将止步于二审。
本届人大常委会还有两次会议,分别是2012年12月底和2013年2月。2月的常委会会议主要是为3月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(全国“两会”)做准备。
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6月二审草案一周后,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《预算法》修正案(草案二次审议稿)在全国人大网公开征集意见,在7月6日至8月5日的征集意见期内,有1.9万多人次提交了33万余条意见。
但是,时间已过四个多月,人大仍然没有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情况,对二审稿是否修订、将吸收哪些意见、会否制订新的草案,至今,均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
鉴于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争议众多,有国务院部门、地方政府及众多学者和公众呼吁,因二审稿条款争议过大,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之前,不应匆忙提交表决,预算法修订应留待下届人大完成。
财政主导修法起草
预算法的首次修订始于2004年,至今已跨越十届、十一届两届人大,修法过程曲折、争议激烈,修法的前期研究讨论、草案起草均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行。十届人大任期内,预算法修订曾被列入2006年立法计划的一类法律项目,计划于当年10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,因人大和政府部门分歧过大最终流产。
十一届人大任期开始不久,再次成立预算法修订小组,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担任组长,财政部副部长任副组长,起草成员单位有十几个,但草案起草至中途,预工委将修法起草工作转交国务院。从草案起草到二审各个环节,整个过程都封闭进行,不仅社会公众对修法内容不知情,预算法专家学者也未能直接参与修法讨论。
去年11月,国务院常务会原则通过预算法修正案草案,并于12月底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一审,内容未见公开。直至今年7月,人大常委会二审结束后一周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终于在人大官网向社会公开二审稿草案,并公开征集意见。
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财新记者表示,预算要求民主和公开,预算法作为规范预算活动的法律,在立法程序上必须遵循民主立法的要求。草案起草时,就应该吸纳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。因为财政部实际上主导了修法过程,结果必然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权力。
专家建议,应该公开二审稿征集意见的结果,并在三审稿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,再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立法宗旨须变
谈及此次预算法修订,学者一致认为,开篇宗旨应改变。草案二审稿维持了现行预算法第一条的表述,以“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,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,加强国家宏观调控”为立法宗旨。
现行预算法1994年通过,彼时中国经济体制正由计划向市场转轨,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刚展开,预算法的立法宗旨更强调预算的工具性职能。
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财新记者表示,经过近20年的发展,预算法修订应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要求,告别国家财政的概念。预算法的宗旨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,实现资金的合理合法配置。预算法要成为管理政府的工具,而不是政府管理的工具。
刘剑文强调,立法宗旨没有改变,导致后面很多条款,从财政体制、预算公开到国库制度等大量授权国务院,本应属于人大的很多权力被虚置。预算核心权力配置,仍未实现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平衡。
值得注意的是,十八大报告提出,“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,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。”刘剑文认为,十八大对预算法提出了新的要求,要求发挥人大的民主审查职能,更有效的监督政府收支活动。
施正文指出,在十八大报告中,“预算”内容出现的位置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此前,党的十六大、十七大报告中,“完善预算决算和管理制度”“深化预算制度改革”这样的表述,均出现在经济体制建设部分,涉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。而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,提到预算内容,并将其作为人大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重要支持。
施正文认为,十八大对预算体制的新定位,意味着未来预算法修订会进一步做实人大的权力,预算的宗旨更加明确,要发挥人大的职能,这要求对当前二审稿的偏离做出修正。
预算公开要完整细化
政府掌管国家的钱袋子,这些钱如何来,怎么花,需要向公众交代清楚。现行预算法未对预算公开作出规定。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,对政府怎么花钱、“三公经费”等问题越来越关注。
近年来,各级政府部门预算、决算公开逐步推进。今年以来,98个中央部门公开了汇总的部门预算表格。但只有完整公开预算、且按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公开细化的预算,公众才有可能实现对政府预算的监督。
此次预算法修正草案中增加一条,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,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,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。
学者认为这点值得肯定,希望公开不要流于形式。施正文称,关键在于公开到什么程度,能否让大家看明白。应按公共预算支出的经济分类公开预算。
在草案初审后的意见反馈和讨论中,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也表示,预算公开缺乏可操作性,建议对预算公开的原则、内容、细化程度、时限、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,以提升预算公开的效果。各级政府应当指定专门部门负责统一公开本级政府各部门“三公经费”的预算、决算情况。
还有地方政府提出,为避免一些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回避预算公开,建议明确“国家秘密”的内涵、外延和认定依据。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陈少英对财新记者表示,预算公开不是静态的结果公开,整个编制、审查、批准、执行的过程都要公开,比如,预算编制前能不能召开座谈会、听证会,让公众参与。
国库管理争权
此次预算法修订,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均删除了“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”的规定。而本应逐步退出的财政专户制度,在草案中进一步明确了法律地位。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财新记者表示,应坚持保留央行经理国库。财政部门在公共预算与政府财务管理中已拥有很大的裁量权。代理制下,央行国库对财政部门负责,除央行国库,财政部门也可以选择商业银行开设账户,存放和管理政府资金。
经理制下,央行国库除了审核收支凭证要素,还拥有审核预算收入缴库、监督财政存款开户和库款支拨等监督权限。央行国库在办理各类款项的拨付时,具备对资金流向实时、逐笔追踪和监督的基础,这有助于发现、纠正和报告处置公款进出国库时的差错、舞弊甚至腐败,能为人大、审计部门提供监管信息。
一旦取消央行经理国库的职权,央行国库只要收到财政、税务等部门开具的收支凭证,应无条件执行,就丧失了审查监督国库资金进出的功能。
央行国库局官员强调,《预算法》修正应明确央行国库监督的法律地位及基本职责。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核算政府全部财政资金收支。此外,应清理整顿财政专户。政府资金实现集中管理和有效监督的重要前提是惟一的政府账户,即“国库单一账户”。
地方政府发债权之争
预算法修订,社会和学界关心预算公开透明、预算权力配置等问题,地方政府则更关注地方发债权限能否放开。现行预算法并没有禁止地方政府发债,但授权国务院做出决定。
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,2009年财政部开始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。2011年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、深圳四地启动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得以逐步推进。
预算法修正草案一审稿中规定,国务院确定的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限额,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。省级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,作为赤字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。但二审稿中,再次恢复现行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,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,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。
对此,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,不理解预算法二审修订稿中,为何否定一审稿中对地方债的积极表述。
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,真实负债情况、财政健康状况难以判断,有些政府部门和专家认为,放开地方发债可能导致风险不可控。
贾康认为,规范地方债务融资,不能堵而不疏,要注意疏堵结合,让市场主体规范地方政府发债。未来应该发展地方阳光融资制度,用透明规范的、受公众监督的,且有利于控制风险的地方债,置换替代地方融资平台,以及一些不规范、风险难控的隐性负债。
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焦建国对财新记者表示,理论上,地方应该享有发债权。虽然现在面临不少问题,但应配合预算改革,要求地方政府有效披露财政收入状况、负债情况,规范地方政府举债。
施正文建议,应恢复一审稿规定,允许地方依法适度发债。但应确定地方发债的指标,包括债务余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、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,国务院核定地方政府的发债额度,在此额度内地方政府报人大批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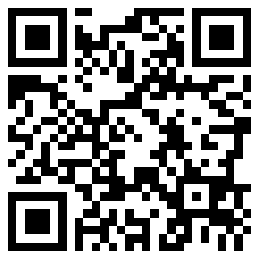


 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3524号
鄂公网安备42010602003524号